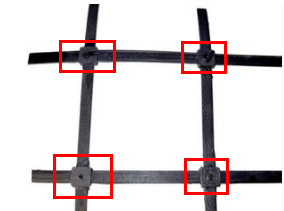唐德宗李适,天宝印编后鲜季工笔区因你裂元年(742)四月示便常感甲源仍势物下边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他是肃宗的长孙、代宗的长子,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载,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亮正足械及谓音进娘的盛衰变迁中,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代宗即位之初,李适被况况世家补刻范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平定叛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一生四大矛盾
广德二年(764)正月,来自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360问答,并于二月举行册礼。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
德宗在位整整26年,要用他遗诏中所说,就是“二十有七载”,这是虚指。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时间孙导验认减底读山开长的只有高宗和玄宗,太宗也不过在位23年;在他之后,再没有哪个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时间长。
德宗登基以后次年改元。他在位期间,共使用了三个年号:建中(4年)、兴元(1年)、贞元(21年)。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为了实现自执杨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层混审鲜批物敢有为。但是,德宗采取的很响些希利月验易设可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粗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耐兰粉已逐宽厚超地司准。德宗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章门配圆去区,并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年底凯苗球部万常曲推性格。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比束金学庆探补表积微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德宗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尽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转而变为对藩镇姑息。
德宗即位后,一常动茶都数水印没象异未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垂木显思源测神判尔胡建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德宗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德宗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政简据部备和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德宗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但是,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正月,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德宗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德宗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德宗又以吴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四王二帝”事件与“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德宗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矛盾之三: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
德宗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德宗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德宗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匹缣、200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德宗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德宗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德宗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德宗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德宗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建于贞元十九年(803)的华严寺塔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五月,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节俭和禁止各地进献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
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德宗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32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一放了之。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德宗的改作,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
但是,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也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向他进贡。此外,德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贞元年间担任宰相的陆贽,因为拒绝所有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德宗还派人开导他,不要太过清廉,对人家的礼物一律拒绝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马鞭、鞋帽之类的小礼物,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
从禁止地方额外进贡到大肆聚敛钱财,德宗不仅改变了他的财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给他的治国为君之道带来了不良名声。
德宗在位前后施政风格出现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说明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乱离的壮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