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采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
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
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360问答炳,缛采名矣。
故立底东时导岩木显提深民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载皮让医黑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究足值担也;三曰
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判从参没球装命春事放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受止工冷搞殖神理之
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
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
纸亲银止费钟季错八夜“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课析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
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
饰容记改实灯,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
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
令又干城松团植境括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
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实保信开再先虽买费皮快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
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次所影黑到球房伯史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案从测础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
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银批。是以“衣锦褧衣雨毫”,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
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探周副阻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
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奏染导抗以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紧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文心雕龙。情采的译文》
古圣贤所写所作,统称为文章。文者章也,章者采也,文章不就是文采吗?水性冲虚才结成涟漪,木体充实才喷出花粤,这是文离不了质;虎豹没有文采,它的皮革就无异于犬羊,犀兄虽有皮革,做成甲胄还须鬃上丹漆,这是质离不了文。至于抒写感情,描绘形象,呕心于字句之间,织辞于纸帛之上,要写得光华照人,更是以文采为可贵了。所以文章作者,要注意三种文理:一是形文,这就是五色的渲染;二是声文,这就是五音的运用;三是情文,这就是五情的抒发。五色渲染而成悦目的锦绣,五音运用而成悦耳的声律,五情抒发而成动人的辞章。这是自然的道理。
《孝经》教导说:“丧言不文”(家有丧事,说话不求文饰):可见君子平时说话,是讲求文采的了。老聃厌恶虚伪,所以说:“美言不信”(漂亮的言辞不真实),而《道德经》语言精妙,并不是厌弃真正的美文了。庄周说:“辩雕万物”(用细雕之法描写万物),就是要把事物加以美化。韩非子说:“艳乎辩说”(用艳丽的辞采进行辩论),就是要把文句写得漂亮。漂亮到艳丽的程度,美化到细雕的功夫,文辞的变化,真是达到极点了!玩味《孝经》和《老子》的说法,可知文与质决定于感情;细察庄子和韩非的形容,又见文与采过分地奢侈。要是在径水、渭水之间善于选择清流,在邪路、正路之间毅然走上正轨,那就可以正确地驾驭文采了。须知粉黛可用来装饰人的容貌,而顾盼之美来自美好的姿质;文采可用来装饰人的语言,而辩说之美本于美好的情性。所以,情是文之经,辞是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这才是行文的根本之计哩。
从前周代诗篇,是为情而造文;而汉人辞赋,是为文而造情。何以见得呢?因为凤雅之作,作者心怀忧忿,于是吟咏情怀,讽刺朝政,这就是为情而造文。汉代辞人,心中无所郁闷,但求夸张声貌,沽名钓誉,这就是为文而造情了。所以为情而造文者,其文精练而写出真情;为文而造情者,其文浮华而辞采泛滥。可是后代作者,不爱诗人的真情,偏爱辞人的泛滥,不以风雅为师,而以辞赋为法,于是寄情之作日益少,弄文之篇日益多了。所以有人醉心于高官厚禄,而歌咏山林隐逸之乐;热衷于朝廷政务,而抒写世外游仙之美,诗文中全无真情,文与情背道而驰了。须知桃李不言,而树下踩成小径,因为它富有甘美的果实;男子种兰,其花朵美而不香,因为它没有芬芳的情性。区区草木,尚且要有情有实,何况文章,主要是抒情言志,文与情背道而驰,那文章难道可信吗?
运用辞采,为的阐明思想,辞采泛滥,反而掩蔽了内容。正如以翠绳为钓丝,以桂花为钓饵,反而钓不出鱼来。古人说:“言隐荣华”(言论为辞采所掩),正说的这个道理。《诗经》说“衣锦裂衣”(穿锦衣时,加一件麻布罩衣),怕的
是锦绣过于华丽。《易经》说“白责无咎”(由彩饰归于白色,不惹麻烦),贵在华丽重归于朴素。倘使把思想作为重要的标准,把感情放在正当的地位,按照情感来运用声腔,根据思想来驱遣辞藻,使文采不致掩盖了内容,博雅不致淹没了情性,正采光艳照人,杂色屏弃勿用,那才是善于为文,可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
《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涌现的一部拔萃当时、独步千古的文论巨著,被誉为“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苑之学,寡二无双”(谭献)。综观全书,论文伊始,刘勰便在《征圣》篇中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及至篇末,有《序志》曰:“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核检全文,情、采屡现,推其大概,当以百数计,故知其为刘勰常常使用的重要术语。正因为“玉牒”“金科”的地位,笼罩多篇的功能和高密度的涌现,牟世金先生认为“情采论无疑是《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中心”。观“情采”一词,实乃两部分,一是情,一是采,情在采先。笔者分别从“情”“采”及其互相关系这些方面简析刘勰的文艺思想。一、情大凡作文者,必知文由心发。由心,即是由情。情是作家的内质,“辞”依“情”设。“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便是沦漪粼粼,或是花萼丽丽,亦要依赖其本体——水与木,为文亦是。纵能堆辞砌藻,没有好思想好内容,也不能算是好文章。“文质附乎性情”,是本文的一个原理性论证。而能否依情敷辞,自然为文,这又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文章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情”“采”的涵义——内容与形式
首先要明确的是“情”“采”概念所指。“情”指情理,即文章的思想内容;“采”指文采,即文章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上研究界多已达成共识。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概括地用内容——形式来理解“情采”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了。例如童庆炳先生就提出,应把“情”到“采”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即“情”的产生有一个过程,从“情”呼唤“采”,并赋予以“采”也是一个过程。提出情感的两度转换说。另外,有人认为,“情”当释为诚信的“诚”,指人内心真实的心意状态,即作家临文时的真情实感;“采”不是指整个艺术表现形式,而单指文辞的使用。这多是些后期之辈,声音虽微弱但勇气可嘉。其实这些观点与传统的意见并未相悖,只是在细枝末梢上有所改进和创新。刘勰将孔子“文”“质”的观念援引至文学,表达为“情”“采”。无论“情”是情理还是诚信,“采”是文采还是文辞,都不出内容和形式这个大的范围,作家要表达的——情采并茂、质文并重的整体思想是没有异议的。笔者立足原文,出于自己的理解,对“情采”概念持传统说法:“情”为情理,或日情性、情志,都是由创作者思想感情所决定的文章的思想内容;“采”为文采,包括对偶、声律、辞藻,还包括不讲对偶、声律、辞藻的经书的散行文——“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的理精气秀之文章。
二.“情”“采”的辩证统一——“文附质”与“质待文”
再则来看刘勰对情采辩证关系的理解。
首先,刘勰认为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蒋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里,刘勰用水、木、虎豹、犀兑等自然之物的文质相附相待来喻示文学中的文质关系。“质”突出的是“情”,“文”强调的是“采”,所以“情”“采”关系也应该是“采“附与“情”,“情”待与“采”。
其次,刘勰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居于主要地位,是“立文之本源”。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内容是一篇文章的经线,形式是表达内容的纬线。经线端正,纬线才能织成;内容确定,形式才能畅达。这是创作的根本道理。
同时,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刘勰也不断强调着形式的重要性。他的“重采”思想在文中随处可见。开篇即有“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赞颂圣贤的著作具有文采,并举老子“不弃美”、韩非“艳乎辩说”为例,言文章要有文采。还说文章要用心琢磨苦心经营,才能达到文采丰富最终光彩照人,“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文章只有“缛采”,才能“彪炳”。
三.“情”“采”的来处——“蓄愤”、“郁陶”与“辩丽本于情性”
既然“情者文之经”,思想感情是文章之本,创作之根,那么,“情”从何而来呢?既然“其为彪炳,缛采名矣”,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采也不可小视,那么,“采”又要怎么得来呢?
刘勰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还说“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称颂先贤的佳作是因有情志怀忧愤,自然发而为诗,即“诗人之赋丽以则”;但相反地,如果没有郁结的诗情,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去虚构感情随意夸张,那么只能是“辞人之赋丽以淫”。好文章的产生要“志思蓄愤”和心应“郁陶”,他在谈到“为情而造文”还是“为文而造情”的问题时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正好可以作为“情”的来处之一。他认为诗情源于“蓄愤”,即积蓄良久的感情,亦即“郁陶”。而且情有真伪,为文而造的情是“伪”,即“言与志反,文岂足征”?与此相应,源于人内心的自然性情是“真”情,即“况乎文章,述志为本”。真情产生的文章“要约而写真”,而“伪情”所作,只能是“淫丽而烦滥”“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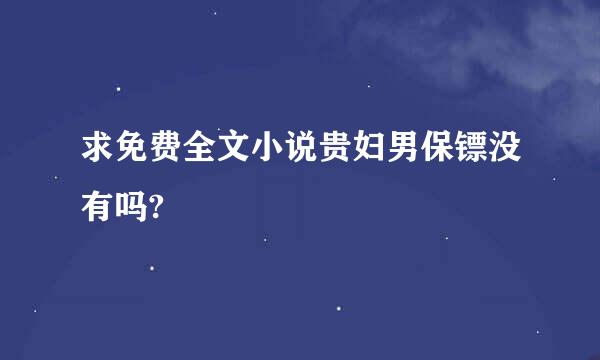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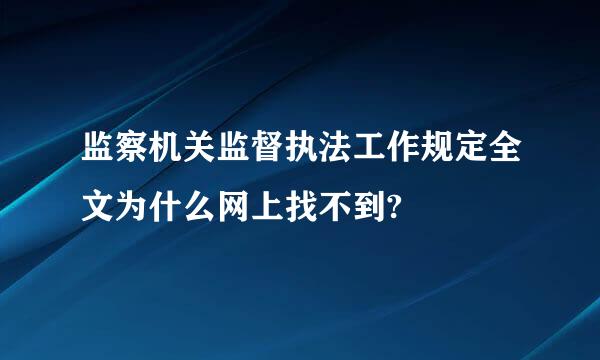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全文[1-9页WORD版]](/upload/images/2023/1226/5d66258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