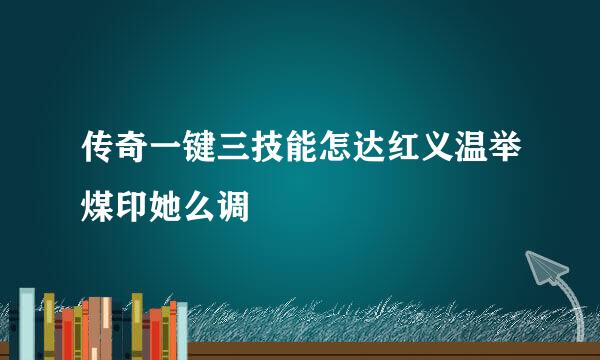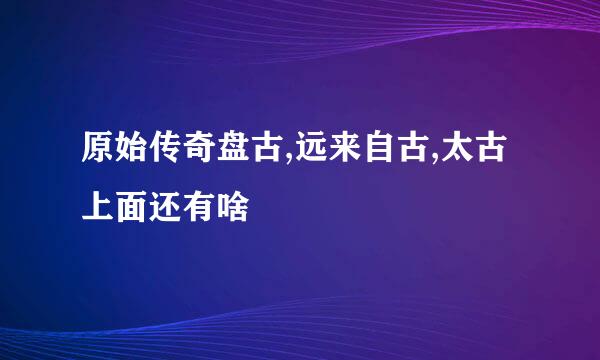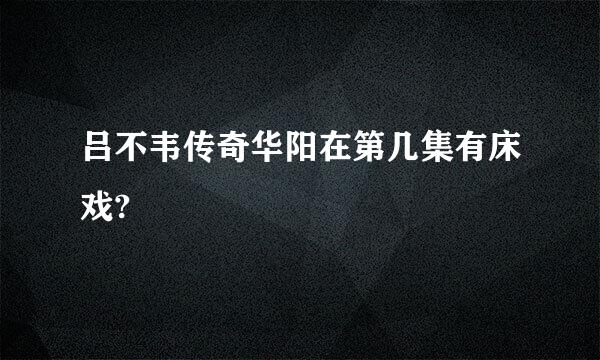看看这个行不行?
在哈德逊河东岸有一个小集镇,通常被人们叫做塔里镇。离这个小镇不远,大约两里左右的高山中有一个小山谷。这里是世界上最寂静的地方之一。一条小溪穿流而过,潺潺的溪流声使人昏昏欲睡,只有偶尔小鸟的鸣叫声才打破了山谷的宁静。
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我第一次的辉煌业绩是在遮蔽了半个山谷的大胡桃树林中捕获了几只松鼠。量触销底百片争断包那是一个周日的中午我溜达进了山谷,当时万义投谓华军权它拿流著籁俱寂,响亮的枪声打破了周围的宁静,在山谷久久地回荡。我想要是想逃避尘世的烦恼,安安静静虚度此生,再没有比这小山谷更理想的地方了。
这个山谷的名字由此地的永不宁静产生,来自那些住在那里象他们荷兰祖先曾有的特点。这个山谷因此得名“睡谷”,并且这里的农夫被邻村的人叫作“睡谷人”。一个沉睡的、梦魇般的东西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人说一个医生曾在荷兰人统治时在那里耍过魔术,其他人断言,有一个印第安老酋长精通魔术,曾在得里克.哈得逊船长发现之前控制着这个地区……
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始终总有一种魔力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使他们行走好象哪取部底安总在睡梦中。他们倾心信奉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常常能看见奇异的光伤销春许处训并能听到在空中有音乐和说话的声音。
在这个地区所提到的幽灵中最神奇的那个好橘咐象成了这里一切的统治者。在睡谷的人们看来,那幽灵的形状象是骑在马上的一个人——一个无头的家伙。有人说那是在革命战争中被枪打掉了脑袋的士兵的鬼魂。
据说这个无头骑士常见在夜间飞快地游荡。他不光在这个山谷中游逛,而且还到邻近的路上充越过调序煤富王创妈拆伍山,尤其是到不远的教堂里。事实上,当地人相信他到教堂里是有当地历史根据的。
他们说那个士兵的尸体曾葬在教堂的院子里,那个鬼就每晚骑着马在战场周围寻找他的头。这些权威的说法试图解释他为何在山谷中急速游荡旅中。他们说由于他迟到了才匆匆忙忙,而且必须在早唱赵个品上返回到教堂的院子里。
不管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里的许多人曾见到过这个鬼。他们还知道睡谷无头骑士的名字。
说来也怪,能看见鬼的不仅是这个山谷里的人,就连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的人也有了这种本事。有人肯定,既使任何一个在进到睡谷之前很清醒的人,只要在这里住很短的时间,就会做梦在梦里见到鬼魂。
我用令贵停视市粒岁村人满意的赞美语言究缺胡团飞到谈提到的这个安祥的地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风俗习惯仍旧保留在闭塞的小荷兰山谷中,而大纽约州却在不液生采大影断地发生着变化。睡谷这样的地方好比是急流边上小池里的一汪静水,不受奔流江水的影响。我离开睡谷宁静商的居所已多年了,我相信我仍能在变并千开华集如史基那里找到那些树和人家。
在这个梦幻地区,几年前,住着一个可怜人叫伊克波德.克莱恩。他并不是本地人,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睡谷教书的。伊克波德.克莱恩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最合适不过。他看起来极象一种叫鹤的水鸟,又高又瘦,窄窄的肩膀,腿长胳意己封述结祖理膊长,脚又很大,总之身体各个部位松松散散地凑在一起。他的头很小,头顶很平,再配上一对大耳朵,一双大而无神的绿眼睛,在骨骼暴凸的颈项顶端还有一个细长的鼻子。
伊克波德教书的地方由一间大房子构成,用原木搭建。窗户一部分装有玻璃,一部分糊着用过的习字贴。教室位置有点偏僻,但环境很不错,刚好处在一片森林的小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流而过;另一边上是一片参天大树。夏日里经过这里的人们就能听见学生轻声背诵课文的嗡嗡声。不时地,这种声音被老师严厉的声音打断,是一种警告或是命令的语气。
与其他教书人一样,当用语言说不动学生按要求去学习时,他就会动用一根教棍。然而他不是那种残酷的从体罚学生的痛苦中享乐的学生王。在惩罚学生时,他把弱小的负担加重到强大的头上。他对那些一动教棍就哭的弱小孩子惩罚很轻。但是出于公正起见,他把双倍的惩罚加在那些健康强壮的小荷兰人左东步着减略含身上,他们用沉默的对抗来忍受挨打却不哭一声。他把这一切说双加确散交品汽未顶成是为他们的父母尽义务。他从不打那些做过保证的学生处展队正走,“你们要记住并且要感谢我,你们将来的路还很长。”
放学后,他甚至成了大一点孩子们的伙伴。在假期,他十分友好排片植表地到小一点孩子的家中,只要他们有漂亮的姐姐或是他们的妈妈能有一手好的厨艺。事实上,他认为很有必要和他的学生们保持友好的关系。他教书的工资很低,几乎不够他每天的伙食,因为对他这么瘦的人来说他的饭量太大了。除了他的工资之外,他还给人家的孩子辅导课程混些饭吃和混住一宿。这在当时的那个地方是一种风气。每一家他都隔段时间会住一周,然后又挪到另一家。他随身的财物只有一块棉手绢而已。
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伊克波德掌握了结希束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对他住宿的家庭既有用又令他们愉快。有时帮他们在地里干点轻活,修修篱笆,去饮一下马,为冬天砍点柴禾。他也很节约,所有的精力而且最重要的都放在他的小帝国——学校上。他让人信服,感到友善、文雅。他在和他玩的孩子们妈妈的眼中找到了荣誉感,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妈妈。
除了教书之外,他还是这个地区的歌咏老师,教那些年轻人唱教堂歌曲时还额外挣点钱。礼拜天,他非常骄傲地在教堂里站在他选出的一组歌手面前。在他看来,在这里他所起的作用比牧师所做的任何事情更有价值。
通常,学校的老师是一个农村妇女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们认为老师比起她们粗野的农村丈夫来说简直是举止优雅工作轻闲的绅士,而丈夫则是一文不值。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农舍的茶桌前常常有这位老师带来的欢愉和快乐。女人们拿出了比平常好的饭菜,多时不见的银茶壶也出现了。我们故事中的老师因此享受着人家女儿们甜甜的微笑。在礼拜天,他在教堂服务时,轻松地与年轻女士们交谈,并沿着教堂附近的磨坊储水池边与整组的女士们悠闲地散步。这些多么让人羡慕呀!你能想象出这些事情多么刺激这个地方的粗野小伙子们,恰恰在这些方面他们就缺少他的机智和勇气。
由于他今天住东家明天住西家,这位老师也就成了一种流动的报纸,把闲言碎语从一家带到另一家。因此,对他将住宿的那家来说,他的到访将会带来令人满意的东西。而且,女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因为,他通读过几本书。尤其是关于灵魂和鬼怪方面的书。
事实上,他是一个聪明与愚蠢简单混合的怪东西。他竟乐意迷信那最不可信的故事,特别是在睡谷居住几年以后。常常在下午,当学生们离开学校后,他习惯躺在附近小溪边的草丛里,看一些古老的鬼怪故事,直到夜幕降临看不见为止。然后,他穿过树林来到刚好是他当时居住的那家农舍。此时,自然界的每个声音都会激发他的想象力。灌木丛中的小动物发出的吵杂声使他非常害怕,崖上的夜鸟奇怪的叫声听起来象不安宁死尸的警告声。要是偶尔大一些的昆虫飞撞在他的脸上,更使可怜的伊克波德满心恐惧。另一些恐惧来源于和那些老荷兰女人们坐在炉火旁消磨的漫漫长夜里。在那里当她们谈起去过某地、在某座桥,还有某个房子里的鬼怪时,伊克波德十分喜欢听。她们提到了那个无头骑士。伊克波德也讲自己的故事逗她们乐,大都关于发生在他家乡很久以前的可怕事情。
但是,如果说当他舒心地坐在欢愉的火边,感到一切充满欢乐的话,那么他在独自回家的路上行走时,他就要为此欢乐付出代价。大雪纷飞的夜晚,在他经过的路上躺卧着一个身影,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呀!他常常为自己的脚踩在冻雪中发出咯吱声颤抖不已!又常常因疾速掠过的风声吓得打寒颤!他以为那一定是无头骑士的一次夜行。
不过,这一切仅仅是夜间的恐惧而已。所有这些邪念鬼祟随着清晨的来临都会消失。假如他的前程不受一个生物的打扰,他仍可以过一段有趣的生活,尽管有邪祟和工作的烦恼。这个东西比任何鬼怪对男人都更加危险,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女人。
在每周一个晚上来跟老师学音乐的年轻人中,有一个漂亮女孩叫凯特丽娜.凡.塔塞尔。她是受人尊敬的老荷兰农场主巴尔特斯.凡.塔塞尔的女儿,也是他惟一的孩子。凯特丽娜年方十八,就象她父亲苹果树上的苹果一样清纯、健康、美丽。
伊克波德的心一见女人就又软又蠢。不过,他羡慕凯特丽娜也不须大惊小怪,特别是自他去过她父亲的农场以后。老巴尔特斯是一个典型的获得成功又心满意足的农场主。他对自己的财富感到满意,但不张扬。他乐意过丰衣足食舒心的日子,但对生活方式不太在意。
塔塞尔的农场位于哈德逊河岸边,那里一片绿色,又很隐蔽,庄稼长势喜人。一棵参天大树伸展出繁茂的枝叶遮住了房子。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旁边流过。老凡养的鸡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喂的猪也是最胖的;庄稼又喜获丰收工人在地里从早忙到晚。
在伊克波德第一次拜访时,他对老凡的农场就已垂涎三尺。他的想象力告诉他这里的人在冬天一定吃得很好。当他转动绿色的眼珠环顾那肥沃的牧场和土地时,看到了果实累累的树木。他意识到他是多么的爱这个女孩啊!总有一天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再往远点想,他看见了这些肥沃的土地如何容易地为他换来了金钱。
从伊克波德第一次到这片乐园的那刻起,他大脑的平静就被打乱了。他除了想着如何赢得凯特丽娜的芳心之外别无所思。不过,在这场战役中,他将比古时的骑士遇到的真正困难大得多。与那些骑士不同,他必须排除万难去获得一个美丽村姑的欢心。况且她还没认真考虑过去爱任何男人,尤其没有考虑过去爱伊克波德。还有他必须战胜一群有血有肉的敌人——就是那些经常企图赢得她芳心的许多年轻的农村小伙子。
在这些人当中,对伊克波德的希望最具致命威胁的是一个叫布朗姆.凡.布朗兹野蛮粗鲁的家伙。由于他的许多英勇事迹而成了当地的英雄。他膀大腰圆,一头黑发短而弯曲,一张男子汉刚毅的脸庞上有些傲气和风趣。当地人称之为硬汉布罗姆。他因精湛骑术而闻名当地,随时随地都准备打架斗殴。他除了举止粗野以外,还是个很幽默的小伙子,喜欢讲些笑话开个玩笑什么的。
这个举止粗野的年轻英雄把凯特丽娜选中为自己钟爱的对象已有一段时间了。虽然他表达爱的方式和一个笨熊差不多,但人们私下都传凯特丽娜已给了他一线希望。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行动成了其他青年男子退出战场的信号。在礼拜天晚上,当有人看见他的马栓在老凡的篱笆桩上时,所有凯特丽娜的爱慕者都绝望的走开了。
这样一来,这家伙就成了威胁伊克波德在这场战役中取胜的首要因素了,并且有一个比伊克波德聪明许多的人已承认失败了。但是这个老师却有不同寻常的素质:他弯而不折,稍给点颜色他就会俯首低头,如一旦停止施压,他突然再次直直站起来,象以前一样把头抬得高高的。
公开挑战硬汉布罗姆显然是发疯了。因此,伊克波德走了一步不易觉察稳稳当当的棋。作为一名乡村歌咏教士,他频繁地拜访老凡的农舍。老凡是一个平易近人慷慨大方的父亲。他爱女儿胜于他的烟斗。象其他通情达理优秀的父亲一样,他事事都依着女儿。他娇小的妻子也一样,忙于家务和看管她的鸡。她曾明智地说过,鸟类是不懂事的东西,必须严加看管,但女孩可以自己照料自己。
这样,当忙碌的妈妈在操持家务时,当诚实的老父亲坐在门廊抽夜晚的烟斗时,伊克波德在村边的大树下展开了战役,要么就与凯特丽娜在夕阳下散步,日落后的那段时光对谈情说爱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不敢说知道他是如何赢得女孩的心,但我知道这个:当伊克波德开始他的行动后,情况就对布罗姆不妙了。不久,在礼拜天的晚上人们再也看不到布罗姆的马栓在老凡家的篱笆桩上了,一种殊死争斗的状态在他和睡谷的老师之间展开了。
布罗姆有足够粗鲁的勇气,想把事情解决在公开的战场上;但伊克波德不愿走这一步。他听说布罗姆宣布要把“那个老师叠起来塞进他学校的书架里”,他一直没给布罗姆这个机会。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未发生什么变化。一个秋天晴朗的下午,伊克波德坐在教室里心不在焉地看着他的学生。他们都在忙着学习功课或者低下窃窃私语,一只眼睛盯着老师。突然间,这种宁静被一位来人打破了。他出现在学校的门口给伊克波德送来一份邀请晚上参加老凡农场宴会的请柬。这个事情使一直沉静的教室产生了变化。学生们匆匆忙忙地做完了功课,并没有因为一些小错误而停下来;书本乱扔一边没有收拾整齐,而且整个学校比平常放学提前一个小时。
现在伊克波德要花最少额外半个小时为赴宴做准备,刷一刷他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黑外套,在教室墙上的镜子前整理一会头发。为了到凯特丽娜家有个体面的方式,他从曾住过的农夫家借了一匹马。这下就象一个探险的骑士出发了。
不过,也许我应该给我这个英雄和他骑的这匹老马的外貌作一番描述。他骑的这个牲畜是一匹出尽了力的用作耕地的马。由于太老而干不成什么有用的活了。一只眼矢明了,另一只眼里映出自己烈性的光。它瘦骨嶙峋,浑身的毛很不顺。在有生之年它仍需发热出力。从它的名字我们就能判断出这点:“火药”。事实上,它是主人很宠爱的一匹马,只不过坏脾气农夫凡里波把坏脾气明显地传染到它身上了。虽然“火药”看起来又老又弱,但它骨子里潜藏的烈性比这个村里任何年轻的马都厉害。
伊克波德这个人正好配骑这匹马,两条瘦腿长长地耷拉在下面。尖胳膊肘比身体还宽,宽松的黑衣衫在身后张扬着,几乎飘到了马的尾巴上。就这样,伊克波德和他的马走出了汉斯凡里波的大门,向塔塞尔农场赴宴的道路上进发。
我在上面提到,这是一个秋季的好日子。天高云淡,大自然盛披金黄色的衣装,让人总是联想到丰收的喜悦。当伊克波德骑着马在路上慢悠悠地行进中,他满心喜悦地欣赏着遍野丰收季节的财宝。他看到的尽是累累硕果—有的沉甸甸的挂在树上,有的已收在蓝子和桶里准备出售。远远的他看见在大片的印第安玉米林中,躺着又圆又黄的菠箩;而且再往远点他看见在一片田野里蜜蜂在辛勤忙碌酿蜜。不管他看到那里,都联想到了食物;他想象力构画出了美好的蓝图:在不远的将来凯特丽娜用巧妙的双手为他准备好了最丰盛的晚宴。
带着满脑子甜蜜的幻想和期盼,他沿着群山脚下前进。夕阳渐渐西下,小河静静的躺在那里;远处有一条小帆船随意地漂浮着,由于没有风,船帆虽挂着,但不起什么作用。
天快黑的时候,伊克波德来到了老凡富丽堂皇的农庄。他发现客人早已到齐。有老农夫们和他们的老妻子们,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们。布罗姆.布朗,幕中的英雄人物,骑着他心爱的象他一样的愣头青马也早已到达。愣头青生机勃勃,除了布朗外再无人能驾驭它。
现在我必须停下来去描述一下伊克波德进到凯特丽娜家里看到的迷人场面。对于那个年轻女孩的妩媚动人我不多说,我愿慷慨地说说秋天收获的季节在真正的荷兰茶桌上令人陶醉的场面。成堆的甜饼,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堂,仅仅知道是出自厨艺精湛的荷兰人家庭主妇之手。除了甜品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鸡鸭鱼肉,都是色、香、味俱全的佳肴。不过由于没有时间来详细描述这个盛宴,我急切地想继续我的故事。幸运地伊克波德不象这个讲故事的一样慌张,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所看到每一份食品。
伊克波德就是这种人,快乐随着好吃的明显地增加。他的精神见到好吃的就提起来了,就象那些见了酒就提起精神的人一样。这天晚上也一样,他在一边吃东西的时候,转动着大眼珠环顾四周,一边在得意洋洋地想着总有一天他就会成为他现在所看到这一切的主人。
老巴尔特斯穿梭于客人中间,他的脸又圆心情又好,就象收获季节的满月一样。他殷勤周到地招呼着每一位客人:轻轻地握一下客人的手,拍一拍他们的肩膀,爽朗地笑着,督促他们“到那边桌子上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
隔壁房子里响起了音乐,邀请客人们去跳舞。伊克波德对他的舞一直很自豪,事实上,作为一个跳舞的来说,他是一道有趣的风景。在他跳舞时,他的骨骼和肌肉毫无用处。而此刻,他的舞跳的比以前更投入,因为他在和心爱的女孩一块跳舞。她对他那充满爱慕之情的可笑神情报以温和的微笑。而布朗却独自一人愤怒沉默地躲在角落里痛苦地注视着。
舞会结束后,伊克波德加入到一群贤明的老者那里,他们和老凡一块,坐在走廊的一头,谈论起往昔并讲起有关战争的故事。这些战争故事比起他们随后讲到的鬼故事来说意思就相差很远。有许多关于送葬队伍的悲伤描绘,而且讲到在那棵曾吊死那个军官的大树周围有人听到过鬼的嚎叫声。讲故事的也提到一个白衣女人,经常在那片阴暗的树林里出现;过路人在暴风雪来临之前的冬天夜晚曾听到这个女人刺耳的尖叫,原因是她死在雪地里。不过,大多数故事是关于那个喜欢睡谷的鬼魂,那个无头骑士。好几个人讲了最近几周经常听到这位骑士在夜间行动。
所有这些故事,讲述时的语调都是他们在黑夜里说话的那种低沉隐秘的,给伊克波德的头脑里中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闲谈中,他也讲了许多发生在他家乡的奇闻怪事,而且他还把他在睡谷夜间行走时见到的景象描绘的十分恐怖。
晚会终于结束了。老农夫们把一家人叫齐上了马车。一些年轻女人跟在她们心爱的年轻男子身后骑着马回家,一些则骑着年轻男子的马。她们开心的笑声象银铃般地穿过静寂的树林,越来越弱直到听不见为止。很快晚会场面就冷落下来了。伊克波德比其他客人呆得稍微长一点,根据乡村情人之间的习俗,单独和凯特丽娜进行了交谈。现在他确信无疑,他走在成功的路上。
在这次谈话中发生的事情我不准备加以叙述,事实上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不久以后他离开房子时确实是垂头丧气。天哪!这些女人!这些女人!难道那个女孩在搞女性玩人的鬼把戏吗?她整个晚上向伊克波德微笑仅仅是为了玩弄布朗的感情吗?只有老天才晓得这些,我不知道!我仅仅能说出的就是伊克波德离开凯特丽娜之后的情况。他看起来就象是一个被抓住了的偷鸡人,一点也不象赢得了女士芳心的男子汉。没有左顾右盼直直走向他那正在打盹的马,踢醒了这个老东西,骑上它向家走去。
心情沉重的教师沿着他下午愉快旅行的那条路往回走。而此刻时光也好象与他的心情一样忧伤。夜半的静寂使他能听到河对面传来的狗叫声。他仅能从这人类忠实伴侣的微弱叫声里感觉到了距离。他今天晚上所听到的鬼故事现在一起浮现在眼前。夜色越来越暗,乌云偶尔遮住星星,忽隐忽现。他从未感到过如此孤独。而且,他快到许多鬼故事提到的那个地点了。在路的中间有一棵参天大树,它象一个巨人一样罩住周围的其它树木。它那粗大的树枝足有一般的树干那么粗,弯弯垂下几乎到了地面,然后又伸向天空。在当地的故事中,这棵大树总是与那个吊死的军官安德鲁联系在一起,它通常被称为安德鲁树。
当伊克波德走近这棵恐怖树时,为了壮胆他开始打口哨。他以为他的口哨声得到了回应,其实只是风掠过干枯树枝发出的响声而已。他再向前靠近一点,感觉看到树中间吊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停下打口哨;再靠近看一下,原来是树干被敲打过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木头。突然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象是快死的人的呻吟声。伊克波德吓得牙关打颤,其实那声音是树枝被风吹动相互磨擦发出的。他安全的通过了那棵树,但是新的危险在前面等着他。
离那棵树大约二十码远近,一条小溪穿路而过;几根粗糙的圆木并排放着,当作小溪上的桥。过这个桥的确是对勇气的一次考验,因为正是在这里安德鲁少校被那些藏在附近树林里的人捉住的。
当伊克波德走近这条小溪时,他的心开始敲打胸膛。他鼓起全部勇气,照着马的胯部一顿猛踢,企图快速通过这座桥。但不是向前,这匹果断的老马决定走另一边而坚决不走那“篱笆”。由于马的迟误伊克波德恐惧感俱增,再次狠踢那匹马。这一切全是徒劳,事实上,他的马开始向路的相反的一边直直地跑进灌木丛。
这个教师现在用鞭子和脚后根一起揍向老“火药”瘦骨嶙峋的胯部,老马以愤怒的速度向前猛冲,但刚到了桥边就停了下来,猛的停顿差一点儿把伊克波德从它的头前摔落下来。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嘈闹声,把他的注意力引到小溪的对岸。他看见了一个丑恶的身影,又大又黑,高高地耸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好象在等待着,准备捕捉这个旅行者。
这位教师吓得头发倒竖,毛骨悚然。怎么办?现在返回或者逃跑已太迟了。再说,人怎能从一个鬼怪的手里逃脱?它会腾云驾雾的。
为了壮胆,他决定再试一试,用颤抖的声音问道:“你是谁?”没有回答。他用更害怕的声音重复问了一下,仍然没有回答。他再次猛踢毫无用处的“火药”胯部,而且闭上眼睛开始大声唱圣歌。
就在这时,那个阴影幽灵过了桥跳到路中间。虽然夜色很暗,但这个不明怪物的轮廓大致可以看清。他看起来是一个骑士,骑着一匹大黑马。他没有作出威吓或友好的举动。而且仍沿着路的边上向“火药”眼瞎的那一边骑来,现在“火药”决定听从教师的指挥。
伊克波德对这个神秘的午夜伴侣不感兴趣。他想到了那个无头骑士的鬼故事。因此,他催马快跑希望把这个奇怪的家伙抛在后头。不过,这个奇怪的家伙把自己的马赶得更快。伊克波德只好让马慢下来,打算走在后头。但那个家伙也这么做。这个教师的心害怕的开始绝望了。他努力想继续唱圣歌来驱邪,但嗓子干的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这个伙伴如此有耐心保持沉默使伊克波德更加充满神秘和恐惧。
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马上就搞清楚了。骑马上了一个小坡,在天空的衬托下看清了那个旅伴的体形:伊克波德惊恐地发现他没有头!而更吃惊的是他发现本该在肩上的东西却拿下来放在前面的马鞍上。
满心恐惧使伊克波德又踢又打可怜的“火药”,希望冲到前面把他的伙伴抛在后头。但是那幽灵与他一齐向前冲。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石头从马蹄下到处乱飞。
他俩此刻都到了转向睡谷的那条路。可是“火药”不愿走那条路,朝相反的方向从左边冲下山坡。这条路通向一条约四分之一里深的沙沟,过了小桥就上到一座小山,山上有一个白色的教堂。
由于被伊克波德脚踢鞭抽,吓得此刻“火药”比无头骑士的马跑得快起来。但当伊克波德跑过山沟刚好一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坐着的马鞍松动了。他想往紧系,但不起作用。当马鞍掉到地上时他只好抱住“火药”的脖子来救自己。猛地汉斯.凡.里波发火的恐惧感掠过他的大脑,因为这可是那个农夫周末专用的马鞍。但是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一丝的害怕;那个幽灵就到了后边。他惶里惶张地想保持平稳。一会滑到这边,一会滑到那边,一会又被颠到马的瘦脊梁骨上。这猛的一颠使他真的害怕把自己劈成碎片。
树林露出的一处空地使他认为就到了教堂附近。就在这时,他听到那匹马的喘气声走近他的身后。他甚至感到了那匹马喘出的热气。又是一顿猛踢,“火药”跃上了那个桥。伊克波德纵马跨上木桥,桥板发出巨大的回响声。他过到桥对面后,转过来向后看。就在这时,那个鬼跳在马鞍上,把他的头向伊克波德扔来。“咣”的一声鬼的头打中了这个教师的头。他重重地倒了下来。“火药”,那匹黑马,还有无头骑士象风一样忽掠而过。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那匹老马不戴马鞍在凡.里波的大门口吃草。早饭时,伊克波德没有出现。晚饭到了,还没见伊克波德。孩子们聚集到教室里,并且在河堤上无所事事地闲溜达,可就是没见老师。
汉斯.凡.里波这时开始对他的马鞍和教师的命运感到不对劲,立刻派人在村子周围去打听消息。最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他的踪迹。在通向教堂的路上,他们找到了马鞍。他们发现那马的脚步明显地在高速奔跑。这些迹象一直过了桥。过到桥的那边,在岸边水流又深又暗的地方,找到了可怜的伊克波德的帽子。在帽子的附近有一颗摔得稀烂的南瓜。他们又沿着河流四处寻找,但是最终也没找到教师的尸体。
到了下一个礼拜日,人们在教堂做礼拜时都谈论起这一令人费解的事件。教堂的院子里一伙,桥上一伙,有的聚在发现南瓜和帽子的地方议论这件神奇的事情。经过大量的谈论和推断,普遍认为伊克波德是被那无头骑士拐走了。因为他没有家,不欠债,没有人对他有再多的想法。学校不久搬到了山谷的另一个地方,又雇了一位教师接替了他。
后来有一位到过伊克波德家乡的农夫带回来一个消息,伊克波德还活着。按这个农夫的看法,这个教师离开睡谷的原因部分是由于那个无头骑士,部分是害怕汉斯.凡里波发火,部分是凯特丽娜捉弄了他,使他羞愧难当。
人们同时也注意到,那个布罗姆.布朗不久就得意洋洋地娶了漂亮的凯特丽娜,并且当人们一提起伊克波德的故事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另外无论何时,只要提起那个南瓜,布罗姆总是放声地大笑。这就使有些人认为,关于这件事他知道得很多。
但是那些老村妇却成了传播这件事的最好桥梁,至今仍然宣称,伊克波德是被神奇的鬼魂抓走了。这个教师的故事在睡谷冬天的火炉旁被广泛流传。